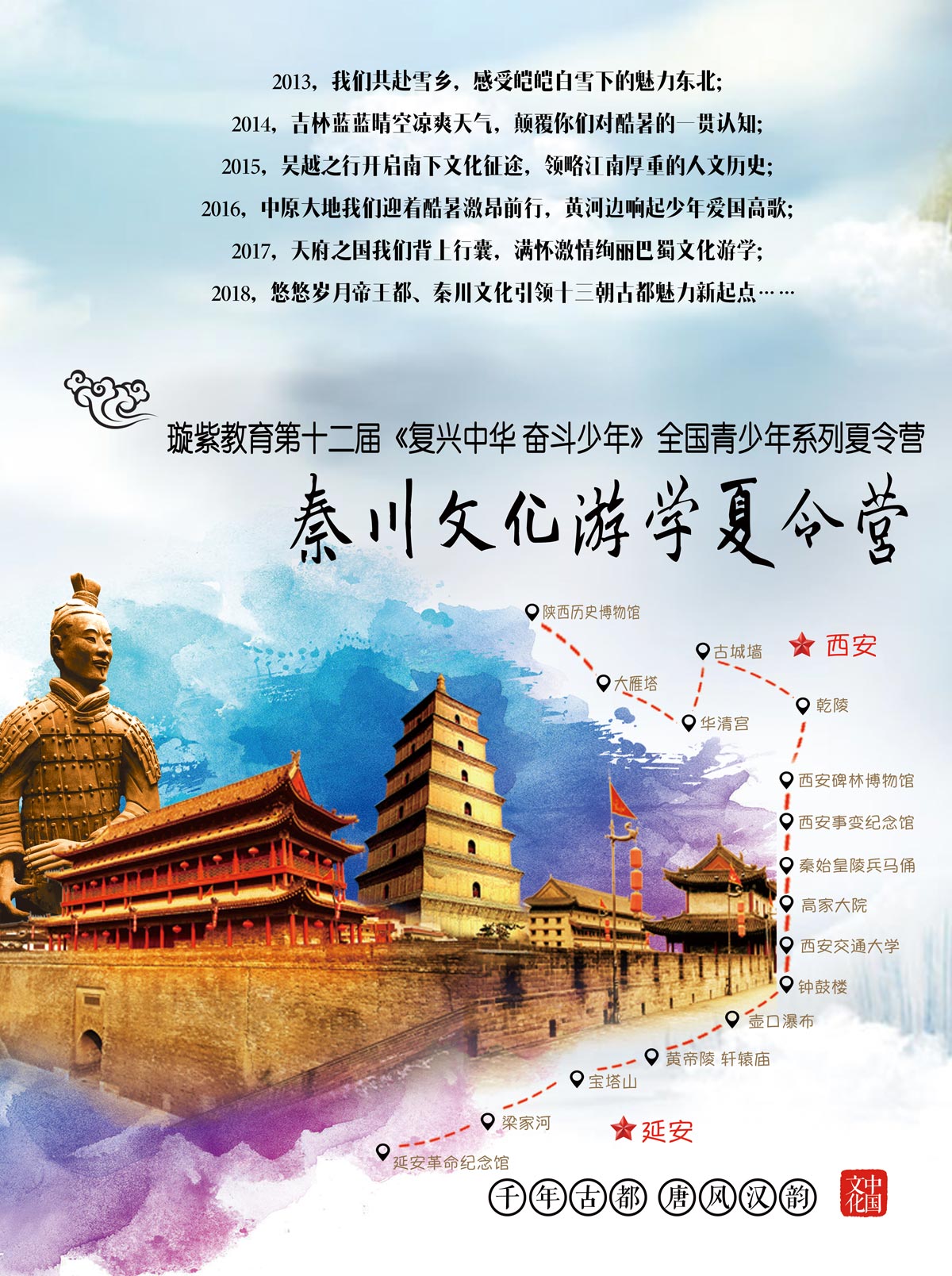一個人的童年生活對他之后的成長有著極大的影響,成年之后,那些困擾你的心結,大部分都需要追溯到童年才能完全看清到底是怎么來的,我們所需要的是療愈我們的童年創傷,那么,我們該如何進行呢?
沒有哪個孩子天生懂事,懂事或許是太深的絕望,因為渴求已經發不出聲音了。作為心理咨詢師,每當我看見現實生活中那些行為過激、偏離常態之人,便能想到他們多半都受到過嚴重的心靈創傷。

當創傷發生,便無法改變,既然改變不了過去,淡忘那些痛苦會令我們好過一點嗎?
答案是并不會。創傷需要被銘記。一個飽受心理困擾的當事人從他現下的心理癥結開始,無一例外都會談到既往的經歷。
而講述痛苦的經歷只是表象,關鍵在于這些經歷向內心深處投下的陰影,不知不覺已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并持續發酵,影響旁人和下一代。
從心理咨詢的角度看,講述只是一個開始,它意味著我們將由此踏上整理和重建內心的旅程,而不是去重復曾經的傷痛。
有人說,往事不堪回首,因為那等于再經歷一次創傷。然而我卻喜歡普希金的話:“那過去了的,終將成為美好的回憶”。
這聽來有些“雞湯”,但只要往事不再成為一種積壓的重負,我們倒是可以從似水年華中追憶到一些凡人的快樂的。
既然我們不可能不負創傷地走出人生競技場,就難免在這場上演出一幕幕“相愛相殺”的戲碼。
不少意識到自身的心理問題來自于原生家庭和早年經歷的當事人,會產生這種想法——都是父母的問題,他們有必要認識到這一點并認錯。
但要讓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承認在家庭中發生了問題,這是很不容易的。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我們無法控制也改變不了他人,包括我們的父母。退一萬步說,即便父母存在問題,他們終于承認并給孩子道歉,但傷害已經造成,這份道歉來得太輕太遲,并不能使當事人得到完全的解脫。
再者,當孩子把注意力集中于期盼父母認錯時,就難以把更多的精力留給自己,實際上是通過內心和父母糾纏讓自己停留在童年的陰影中。
停留是對生命的損耗,反而使得當事人通過犧牲自己人生的方式完成了對父母的變相認同,即永遠生活在父母的影響下。
況且我們“強迫”父母認錯的樣子和父母當年對待我們的樣子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
所以我們搞心理的常把“內省”掛在嘴邊,主張當事人能夠增進自我覺察理清內心的愛恨情仇,進而獲得成長。
如果我們只是從現實層面和父母隔離,并不去處理自己和已經內化了的父母形象之間的關系,相當于是把那部分創傷帶來的痛苦壓抑了,困擾當事人的情結還是得不到解決。

改變到底有多遠?
當一個人具備改變的意愿,并且愿意學習像個成年人一樣付出,而不是和嬰兒一樣單方面索取回報時,也許就將迎來真正的改變了。
人在受過傷后往往會更加沉默專注,無論是心靈還是肉體上的創傷,只要善加利用,對成長都有益處。
好像老輩人常說,生孩子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月子是女人重生的機會,怕是正應了這道理。
當我們面對累累創傷帶來的苦難之時,每一次的自我超越都標志著靈魂前進的刻度。
盧梭創作《晚年漫步錄》時已至垂暮之年,當一個人經歷了大半生波折,老年時不再沉溺于各種喧囂,反而顯出一種近乎透明的心態。
人世,一個既有漫天刀光劍影,又有太多兒女情長的江湖。沉重的精神枷鎖讓人們似乎只有靠記憶和想象才能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以及將要去向何處。
當紛擾肆虐之時,往昔的經歷成為每個人重新建構自身的唯一材料,雖然這些經歷中有災難,有苦痛,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確認自己曾經,并且現在依然在場。
蘇格拉底在《斐多篇》里說,真正的哲學家對死亡沒有絲毫懼怕,因為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學習死亡,生命的終結不過是他所學習的東西成為現實。
這就是說,當人面臨巨大的痛苦,甚至當生命的帷幕即將落下時,他仍然需要從既往的經歷中獲得一種確認,確認自己的存在,我們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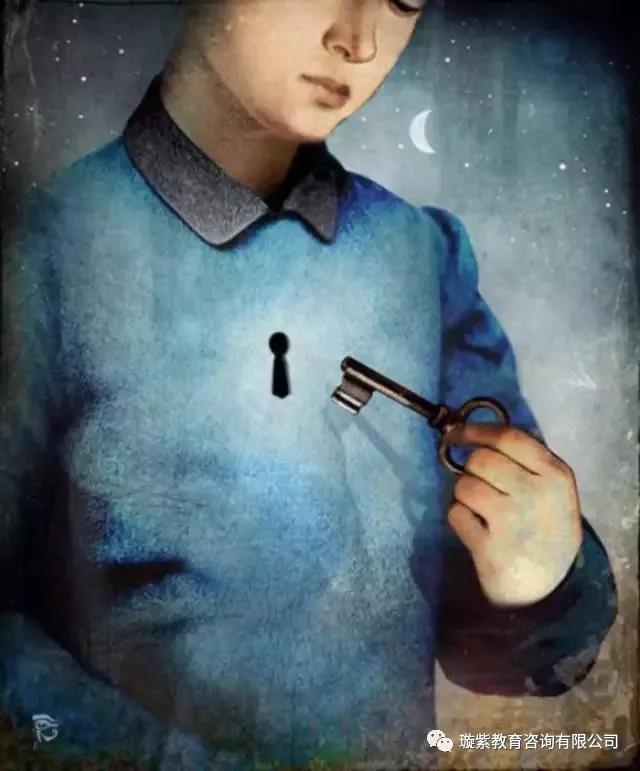
療愈創傷之痛,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學習理解生命和人性。
當你用更客觀更完整的視野與自己和他人接軌時,你將發現你的創傷并非過錯,亦非缺陷,而是導向羅盤,引領著一條更偉大的人我契合之路。
無愛感是普世創傷,自個人內心蔓延至婚姻和家庭,校園及職場,政壇還有宗教,弄得烽煙四起。改變的標志從來不是空談道理,而是你開始真正去理解身邊的人與事,接納自己,愛自己。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慈悲是為他人,更是為你自己。